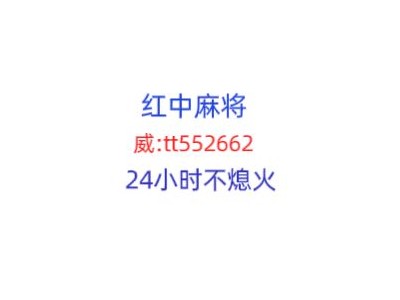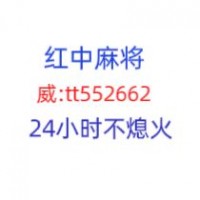%D%A 1.亮點:紅中麻將跑得快微信“群”vy23547-- tt552662---930229533—認準Q微同號靚號其他都是冒充!備用QQ:464870180 %D%A 2.簡介:廣東紅中麻將--四川血戰麻將--二人跑得快1-2元“群” %D%A 3.類型:1塊川嘛血戰麻將,一“元一分紅中癩子麻將,一“元一張二人跑得快15張 %D%A 風是理念的烽火,實際都動道理。風是典范的目標,道路都度蒼山。風是珍愛的禮品,人生都留住精力力氣的萬卷書。 /> 早在一千四百年前的劉勰,對于文章的繼承與創新就有自己獨到的見解。“變則可久,通則不乏”,認識到創新才能流傳久遠,繼承才不致貧乏。《文心雕龍》中的《通變》篇,是專門論述繼承與創新辯證關系的篇章。對于現今的文化創新,仍有著啟悟的現實意義。 “夫設文之體有常,變文之數無方,何以明其然耶!凡詩賦書記,名理相因,此有常之體也;文辭氣力,通變則久,此無方之數也。名理有常,體必資于故實;通變無方,數必酌于新聲,故能騁無窮之路,飲不竭之源。” 是說文章的體制有常規可循,變化文章的方法則無一定之規,怎么知道是這樣的呢?所有詩歌、辭賦、書札、奏記等體裁,名稱與寫作原理都是前后繼承的,這就說明體裁是有常規可循的。文采、語言、氣勢和感染力量等等,須有所變化創新才能長久流傳,這就無一定之規了。文體的名稱與寫作原理各有常規,所以確立體制必須借鑒于過去的作品,寫作中的變化創新沒有一定,所以在寫作方法上必須參酌新的創作,這樣,才能馳騁在無窮盡的創作道路上,汲取永不枯竭的創作源泉。 劉勰還用通俗的比喻說,有的作者象井繩太短,因打不到水而口內干渴,有的作者象腳軟無力而半途停步,這并不是因為文章寫作的道理已經窮盡,而是由于對繼承創新的方法不通曉罷了。討論文章的寫作方法,譬如草木生長,它們的根干都附著在土地上是共性,但受陽光照射的差異,便具有了不同的品格和味道了。 任何創新都有個基礎問題,之所以“口內干渴”,之所以“半途停步”,這都是因基礎不牢而創新乏力的緣故。所以浮躁是創新的大敵。前不久看張澤勇的《胡巖論畫錄》,我非常欣賞畫家胡巖的創新精神。胡巖告誡人們:書畫最忌諱急功近利。書不阿俗,畫不阿貴,書不阿財,畫不阿時。迎合世俗,逢迎權貴,癡迷錢財,追求時尚,最容易失去自我與個性,哪兒還有藝術創新可言。迎合世俗者,作品必然圓滑,逢迎權貴者,作品必然無骨,癡迷錢財者,作品必然輕浮,追求時尚者,作品必然花哨。凡此種種,雖能浪得一時虛名和錢財,享得一時榮華和富貴,哪能經得起時間和歷史的無情淘汰!若想讓自己的生命在作品中延續,創作的作品教化后人,還是要在文化的積淀,生活的積累,觀察的精細,作品的枝藝上下苦功,將自己的生命節律融入在神奇的造物之中,從而孕育出“造理入神,回得天意”的傳世作品。你看他說得多精彩,繪畫藝術創新與文學藝術創新,雖一個用色彩,一個用文字,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,沒有深厚的文化積淀,沒有深入的生活,不克服浮躁心態就談不上創新,胡巖與劉勰的認識可謂有著異曲同工之妙。 劉勰認為《通變》是一種普遍的現象,從黃帝到周朝的詩歌,一代比一代富于文采,這是革新的成果,但在“序志述時”方面,基本道理卻是一樣的,這是繼承的明證。一代一代地既“通”且“變”,才構成了文學發展的歷史。劉勰在《物色》一篇里說得明確而精辟:“古來辭人,異代接武,莫不參伍以相變,因革以為功,物色盡而情有余者,曉會通也”。認為從古以來的作家,一概是先有所繼承,同時又錯綜新舊加以變化,無不是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才取得成就的。通曉繼承與創新的道理,才能寫出景物有限而情味無窮的文章。 劉勰還認為:繼承必須是正確的繼承,有意義的繼承,能夠有助于文學發展的繼承;創新必須是正確的創新,有意義的創新,能夠提高創作質量的創新。如果“竟今疏古”,沒有正確的繼承,就談不上有正確的創新。“斯斟酌乎質文之間,而隱括乎雅俗之際,可與言通變矣”。在質樸與文采之間細加斟酌,在典雅與淺俗之間認真矯正,才可以論談通變的道理呀。 對于怎樣正確繼承,正確創新,劉勰在《通變》中作了明確回答:“是以規略文統,宜宏大體。先博覽以精閱,總綱紀而攝契,然后拓衢路,置關鍵,長轡遠馭,從容按節,憑情以會通,負氣以適變,采如宛虹之奮鬐,光若長離之振翼,仍穎脫之文矣。若乃齷齪于偏解,矜激乎一致,此庭間之回驟,豈萬里之逸步哉!”劉勰認為考慮文章的整體規劃,應該總觀大局,廣泛瀏覽和仔細閱讀古今作品,掌握文章寫作綱領,從中攝取合乎需要的東西,然后開拓文章的思路,設置文章的重點,使文情的發展象乘馬運行,放長轡頭,從容不迫,有節奏地前進。應依據表現情志的需要去繼承古人的成就,根據自己的氣質特點來施展創新,辭采如長虹拱起彩色的脊背,光輝如朱鳥鼓動美麗的翅膀,那就是卓越不凡的文章了。假如局限于個人的一偏之見,欣賞夸耀自己的一得之思,這只能是在庭院中轉圈的劣馬,難道是日行萬里的駿騎嗎! “憑情以會通,負氣以適變,”劉勰既看到了繼承的必要,也看到了創新的重要。繼承不能是“循環相因”的模仿,更不能是“殆同書鈔”。創新不能“淺而綺”、“訛而新”,更不能“彌近彌澹”。只有“憑情以會通,負氣以適變”結合起來,才能使繼承目的明確,使創新基礎堅實。繼承與創新統一起來,互相影響,互相滲透,相輔相成,相得益彰。才能促進文學創作質量和提高文化事業的健康發展。 愛因斯坦曾經說過:組合是創造性思維的本質特征。有人對1990年以來國外480項重大科技創新成果進行分析,發現重新組合式成果占65%,突破式成果占35%。可見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占了絕大的比例。這種創新思維現代名稱就叫重新組合型創新思維。如此看來,劉勰的“憑情以會通,負氣以適變”,可算的上是這種創新思維方式的鼻祖了。 我國研究員許立言、張福奎提出的12個聰明方法,為重新組合創新思維提供了新鮮血液。他們的方法是:加一加、減一減、擴一擴、縮一縮、變一變、改一改、聯一聯、學一學、代一代、搬一搬、反一反、定一定,即通過重新組合事物的結構或事物形成的操作程序,從而達到創新的目的。 劉勰在《通變》最后總結道:“文律運用,日新其業。變則可久,通則不乏”。他說文章寫作的規律周而復始的運行,文化事業要不斷創新。創新才能流傳久遠,繼承才不致于貧乏。劉勰早在一千四百年前對于繼承與創新的論述,是極為難能可貴的。學習劉勰的繼承和創新理論,對于現今的文化創新,對于中華文明的傳承與弘揚,有著功在千秋的重要意義。 一個我要向東,而另一個我要向西,這兩個我立馬就成了敵人;一個我要向東,另一個我也要向東,這兩個我也立馬就成了朋友。所謂的敵與我,如能作如是觀,則還有什么不能為我們所通悟呢?所以我們的這個世界看上去好象五花八門,五彩繽紛,大路上人聲沸沸揚揚,男女老少擁擠在一個城里,可是看穿了,卻又簡得很,簡單得萬物只歸于一,繁華的世界其實卻是一片荒涼,只有一個人在那兒孤獨地變幻著他的臉相和表情,排演著他的情緒和故事,高歌或長嘯,長哭或短泣,生或者死。